《紙花》:童年經驗與女性視角
興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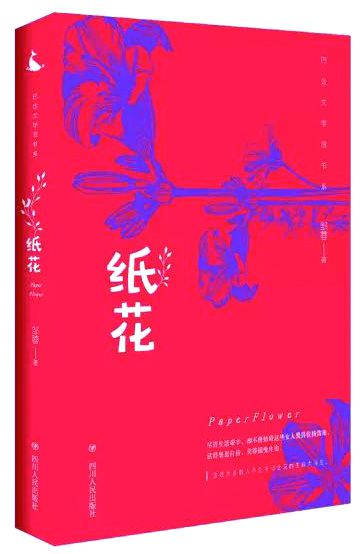
近年來,“70后”作家的創作已經進入了最好的時期。在風起云涌的“70后”作家中, 鄒蓉還算陌生的名字,但是她的創作卻給我特別的感動。小說集《紙花》中的幾個短篇給人印象深刻,也讓我看到了“70后”作家的潛力和價值。
小說《紙花》是集子中我最喜歡的短篇之一,小說寫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出乎意料地冷靜,寫一個鄉村女孩的孤獨和超出她年齡的遐想。這種孤獨首先來自她對自己出生的疑惑——我從哪里來(母親都不記得她的生日,她總是懷疑自己是被撿來的),其次是對死和離別的傷感與不解——親人(兩個親戚被石頭砸死或車禍,死相很難看)或身邊人(一個同學因為結婚回老家,再也沒回來)的死亡或離開。女孩的心是靜悄悄的,甚至是孤寂的,但是卻不斷地被世間的生與死引導和影響著她的生長。這是個敏感早熟的女孩,她生在鄉村,卻有著與眾不同的內心經驗。她對自我、對周圍的事物的觀察和理解都與同齡人格格不入,超越了她幼小的年齡。小說實際上表達了女孩“個體意志”的覺醒,對“自我身份”以及“歸屬感”的質疑。我們知道,自我意識是人類首要思考的抽象問題。這種最初的、對自我身份的懷疑和認同,以及隨著遭際不斷改變的關注重點,貫穿了這個小女孩的成長歲月,即由她對自我的發現、引申到她與他人、環境、社會乃至整個外部世界之間的關系的思考。小說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她在學校門口,握著一把最小單位的零錢準備花出去。因為今天是她的生日,可是沒有人記得自己的生日,包括自己的母親,更沒有人會為自己過生日,所以她決定用這點錢犒勞一下自己,給自己過一個生日。這個女孩究竟有多少錢呢?她不止一次數過,可因為錢的單位太小,始終也沒有數清。小說寫道:“一張五毛的,三張兩毛的,還有四張一毛的,余下的是五分、二分和一分的紙幣,大概有好幾十張。”可總共也不會超過兩塊錢。她將這些錢裝在兜里,鼓鼓的,來到小賣部。她看著琳瑯滿目已經被自己多少次張望和渴望的各種食品,吸聞并辨別著老板娘嗑的瓜子的味道,想象它們在自己嘴里咀嚼時產生的香甜或者咸的滋味。但是,最終她還是悻悻離去——或許是她舍不得將自己好不容易攢的錢一下子花掉,或許是害怕小賣部的老板娘嘲笑她的錢太少而失了尊嚴。
這是個缺乏愛的孩子。正由于此,她在大病一場時產生了幻覺和噩夢。在夢中看到一只手在掐她,她甚至感覺自己的母親在給她的水杯中撒藥。在這個小小的身體里,似乎在思考著人類永恒的問題:我是誰?我為什么存在?我將去向何方? 哲人說過:愛是一種確信,它可以驅逐不安和恐懼。而當她缺乏這種愛的時候,她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她甚至渴望自己掌握一種超自然的能力和預知未來的本領。所以,她的一次無意中的勸告(預言),竟然神奇地讓一個女同學逃過了一起車禍。我孩提時也曾有過類似的體驗,但很難說這就是預知能力,它更像是童年在孤獨與無助中對超能力的一種渴望和幻想,就像《哈利·波特》里的魔法棒,它是孩童時期抵御恐懼和孤獨,認知或者逃避現實及外部世界的一種方式。
《香阿姐的花夜》也是以女孩的視角,同樣是寫她的孤獨與成長,但卻是以一場熱鬧的鄉村婚禮為前奏。作者非常善于細節的捕捉與日常生活的展示,比如寫到村民為酒席而宰豬和剁肉的過程,非常精彩:“那個剁肉的年輕女人,刀也是用得出神入化 ,就跟長在她手上似的,‘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整個人也是跟著這個節奏在抖動,就覺得她自己是很享受這個過程。多看了幾分鐘,又讓人不免擔心,如若女人稍微慢半拍,那個用來剁肉的墩子就會跳起來……”那個表哥教女孩子們習武的騙局也特別可愛,他不但沒有因為這個騙局而失去“我”對他的好感,反倒覺得他是個有趣的人。至少告訴女孩子練點武功,不受男孩子欺負的道理。小說還寫到了親戚鄰里的相聚以及復雜的親緣關系,但是恰恰是這歡快喜慶的場景,反而更凸顯了女孩的孤獨和形單影只。小說里說的“花夜”,其實就是姑娘在出嫁前的晚上,家人及親朋好友要舉辦一場豐盛的酒宴,唯獨新娘不能參加,只能待在閨房里,等待明天新郎的接親。這恰好給了女孩與新娘阿香姐獨處和交流的機會,因為同樣的經歷或命運也在不遠處等待著她,盡管出嫁對這個孤獨的女孩來說也許并不是件快樂的事情。她懷疑甚至不認可阿香姐由父母包辦的婚姻,只能用“勇敢”一詞來為她祝福。她不想把自己的將來托付給未知的人,她希望由自己去面對愛情和婚姻,這個念頭出自一個還未成年的女孩,執拗、獨立而富有個性,卻給我們無法言說的思考和感觸。還有《船殤》中那個執著地編織毛褲的不合時宜的女孩,以及《丁丁貓兒》中那個對死亡懷有童話般奇想的女孩等等,這幾個不同女孩的成長經歷,組成了鄒蓉小說中活生生的女孩群像,也構建了她小說整體的內向視角和樸素感傷的基調與情境。那不濃不淡的孤獨感,彌漫在字里行間,浸透在每個場景和每一個人物的眼神之中。
短篇小說的寫作,每個作家其實都有自己的源頭和路數,鄒蓉的短篇不是來源于莫泊桑和歐·亨利,也非來源于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她更多的來自于契訶夫或者卡森·麥卡勒斯的傳統。麥卡勒斯在《創作筆錄·開花的夢》里說過這樣一句話:“一位老師曾經說過,一個人只應該去寫他自己家的后院。對于這一點,我猜他的意思是一個人應該去寫他最為熟悉的東西。但是,有什么東西是比一個人自己的想象更加熟悉的呢?想象力以悟性組合記憶,以夢境來排列現實。”我覺得這句話很適合鄒蓉的寫作,其實想象力并不一定是特別超現實的東西,而更多是對生活的體悟、敏感,以及作家對人物和故事尤其是細節的捕捉和想象。鄒蓉的小說多半郁結于她的童年經驗——成長中的創傷和精神的隔離感,沒有繁復的情節,更沒有花招式的敘事,它更像是一種封閉性的自言自語式的寫作,但是正因為如此,它的小說常常直抵人心,讓人揮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