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表現,深刻的揭示
——讀寧新路長篇小說新著《轉世天狼》
石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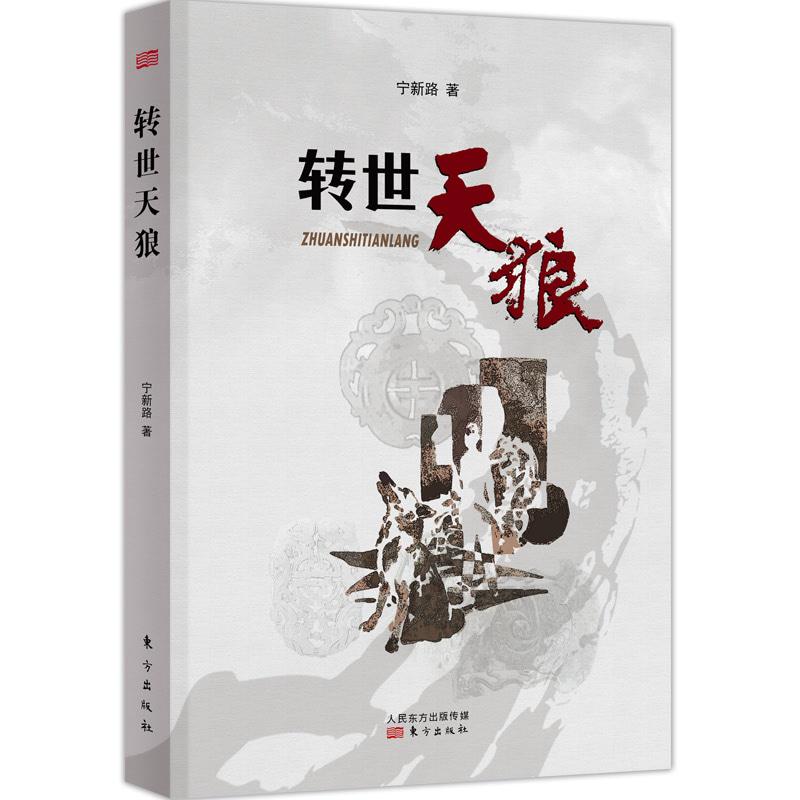
《轉世天狼》是作家寧新路的長篇小說新著。僅從作品的命名來看,便自然使人覺得新奇而欲知其內容為何。我正是抱著這種想法先睹為快地看完了這部二十多萬字的耳目一新的小說。從表面上看,這部從書名到內容都概不常見甚至有點荒誕的作品,但如仔細加以品咂,便會感到在表面上很可能是根據一個民間傳說所演繹而實質上包含著發人深思的人生世相;其獨特的揭示方式仍能夠給人以啟智的警示。因此,我覺得不妨將這部小說視為一部將民間傳說與人生況味相揉合的奇幻小說加以賞讀。
作品的基本表現手法仍是現實主義小說的敘述方式。全書出場高密度的貫穿性人物是開玉作坊的柴大老爺與他的看門管家張鞋娃;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則是張鞋娃的親密伙伴叫阿黃的看門狗。從表面上看,柴大老爺與張鞋娃乃至阿黃之間是絕對的主子和奴才的關系,卻又不那么簡單與單一。那個渾身散發著臭鞋味、活到人生小半截還是光棍一條的張鞋娃,卻能在偶然的情況下被柴大老爺收納和使喚,肯定在他下三賴的表皮之下還有某種“過人之處”。甭說別的,就是那條非同尋常的看家狗阿黃,一般人它都不給好臉色,可唯對張鞋娃卻破例的忠順(可能內心里也服氣)。這除了狗與人之間也有某種“惺惺相惜”之外,骨子里也有強烈的磁場能夠撞擊出火花來。但在最初的一個階段中,柴大老爺主要還是為了張鞋娃便于驅使,可以隨意打罵,乃至當成一件宣泄器具,自覺比較靠得住,所以就連嫖娼時也帶著他,以便隨時聽候差遣。但張鞋娃卻能“閑中偷忙”,他也抽空借機找樂。作者的深刻之處就在這里,他在對人物的刻劃上,從不那么簡單化,淺表化。否則,如果只將柴大老爺和張鞋娃之間處理成黃世仁與穆仁智那樣一個暴主一個惡奴的主從關系,那張鞋娃也就不是“天狼轉世”了。但他們之間也并非一般的狼狽為奸,而是一種層層相疊、環環相扣、相互扭結、難解難分的離奇而又真實的人物關系模式。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作者獨具匠心配置與創造。
奇幻嗎?有一點,卻又如見其真;荒誕嗎?一切卻又觸手可感。柴大老爺的發達絕非憑空而來,同樣有其深厚的背景和他人難及的優勢;這里有百年幾代的精于經營,有兇殘到家的盤剝手段,更有特定的時代背景,國家不幸邪幸,在柴大老爺和他的玉作坊的背后,有日寇派駐軍官,甚至就連日寇軍官小野“寵幸”的妓女小菊花也優勢“借橫”;還有柴太太娘家近親偽政府官員撐腰……這才能使柴大老爺發跡的圖謀無不成功。但同樣是,作者并沒有將作品處理成一般的剝削壓迫“模式圖”,而仍然是通過張鞋娃、阿黃等典型化特征性的描寫,凸顯了權勢方花樣翻新的酷虐。如對玉作者的苦工們無孔不入的榨取、作賤人格的隱身搜身……等等。在這當中,作者絕未忽略了張鞋娃與阿黃犬的“神功”——所有的重要角色在節骨眼上絕不會缺席。
介善惡興衰的轉化規律在任何創作方法的作品中也不可能截然相反,即使在帶有某種荒誕色彩的作品中也不例外。原因很簡單,因為它的基本內核仍是現實主義的。盡管小說中的柴大老爺挖空心思,翻云覆雨,“事業”運作與狂浪享受雙相并舉,似乎有無限精力遠涉四方,一為玉業,二為獵色尋歡,除在他的基地有本宅家室之外,在新疆和田,在云南,在太原,在南京,都有“小家”和妻室。但到頭來,由于“自窩亂,自窩反”,還有此起彼伏的外憂,這位精明強悍的大老爺,最后由于傷病交加,雖然竭力掙扎,終也未能戰勝命運的懲罰而嗚呼衷哉,未能逃脫“自作孽,不可活”的結局。他遺下的除了玉行家業,還有無一缺額的幾個女人。
但“轉世天狼”張鞋娃仍然健在,也許是因為他雖也有諸般劣跡,但靈魂深處仍存有一個純樸尚善的角落,心目中還有一個念念不忘的女人小蓮。這個小蓮在作品中雖“戲份”不多,卻始終是這堆形形色色的人群中罕有的比較干凈的靈性亮色。還有,那條阿黃老狗,盡管瘦弱,還是又回到了張鞋娃身邊;結尾有一段文字意味無窮,不可不引:“張鞋娃由他的老狗阿黃陪伴,等小蓮回來,日子過得平靜而快。可等心上人的日子,卻是焦心的,等得人和狗,越發凄愴,而他仍然等她(從尼姑庵)回來,雖等待回來的期限無限,但他感覺等得很幸福”。
本小蓮在語言風格和表現手法上與其內容非常諧合。語言文字生動舒放,生活化,個性化,色調濃郁;某些方言上語用得適當貼切。有些雖有些俚語恣肆,但憨直中含機趣。作者顯然是追求一種潑辣率真,富有性格化的格調,也是一種不乏探索精神的嘗試。在謀篇和結構中,同樣是以一種旨在生趣活絡而忌呆板滯澀的方式進行組合。在這方面,也有許多值得贊賞的表現。如在交待柴大老爺設置四面八方的“家室”時,有意以回報幾乎相同的文字加以點染,讀來不覺其重復乏味,反而覺得在調侃中含有諷刺意味;同時也反而省卻了許多筆墨,增強了藝術表現的張力。諸如此類,舉不勝舉。僅舉幾例亦不難看出:本小說是新路同志的一部頗為用心之作。
石英,著名作家。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編審,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著有長篇小說 《火漫銀灘》《血雨》《密碼》等70余部,計1000萬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