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是靜悄悄地活著,也準備靜悄悄地死掉——對話李澤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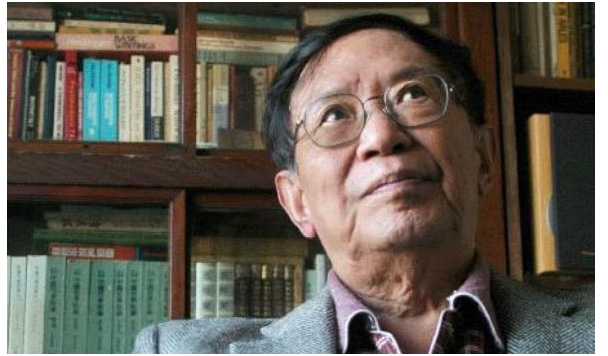
有的人是“蒙啟”,把啟蒙過的東西又蒙起來
人物周刊:以思想界的標準,您可以說是少年得志,20多歲時,就在50年代的美學論爭中成為一派代表。到80年代時,很多人認為您是影響思想界第一人,不管他們支持您還是反對您。
李澤厚:其實在80年代我并沒感覺到自己多有影響,后來知道了,就有點后悔,我應該多去大學里走走。(笑)可是我并不知道,我沒有感覺我是第一。我的書罵的人也非常多,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罵我,搞民運的也罵我。我說,讓時間來檢驗吧。
人物周刊:現在回過頭看80年代的美學熱,是否覺得不可思議?
李澤厚:是啊,古今中外美學都沒這么熱過,所有的學校,包括醫科大學、理工大學都開美學課,甚至還有工廠請我去講美學,我拒絕了。這是很奇怪的事情,也是個很好的博士論文題目。當時美學影響到生活態度和生活規則,有人開玩笑說以前政治掛帥,當時是美學掛帥。
人物周刊:當時為什么會出現這股奇怪的美學熱?
李澤厚:從哲學上來說,美學是很重要的,我說過美學是第一哲學。西方美學很多講的是藝術,中國美學概念比西方廣泛得多,包括人生、政治的選擇。當時美學是權威體制下的解放力量,因為政治禁忌,別的很多東西不能談,美學相對自由,成為一個突破口,引領了時代潮流。到現在,美學越來越物質化了,成了商業化的裝飾品。
人物周刊:您主張“美育代宗教”,以美學安撫中國人的心靈。現在美學逐漸邊緣化了,還怎么發揮作用?
李澤厚:中國人缺少信仰。蔡元培、王國維提出“美育代宗教”在上世紀20年代,過去快有100年了。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問題。現代生活中偶然性增大,人會感覺到命運沒法掌握,人生意義沒法知道。活著就是為了賺錢?賺了錢之后怎么辦呢?為什么活這個問題很多人解決不了。
什么都不信仰的人是危險的,為了自己的利益任何事都干得出來。知識分子完全信宗教的不會太多,因為宗教有很多非理性的東西。我提倡信仰“天地國親師”,結合傳統,再加以現代解釋。它不會像基督教、佛教那么快發展,因為我提倡的信仰不會有那種組織的力量。我反對有的人搞儒教把孔子變成神,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上帝、佛祖都是人格神。我是愛因斯坦那種信仰,就是相信宇宙本身。這和儒家講的“天地”是一樣的。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美學對政治也有影響,怎么理解?
李澤厚:西方政治最高理想是正義,講的是理性裁決。中國文化強調情感和理性統一,合情合理、通情達理,政治上也是這樣。我為什么要提出“情本體”?就是認為中國光講理性不行。中國人勸架不是搞清誰有理,而是講求人際關系的和諧。我舉過《秋菊打官司》為例,秋菊打贏官司傷了人情,并不是最好的結果。
“情本體”是未來的事情。目前中國連“理”都沒樹起來,什么都講關系、講人情、走后門。需要先建立公共理性規范,把“理”建立起來,才能接上傳統講“情”。所以我不站在搞國學的那些人一邊,和國學相關的活動,我統統不參加。他們搞的那些恰恰在阻撓普世價值的建立。
人物周刊:劉再復先生說你們有本整理中的書叫《返回古典》,請談談你們的“返回古典”。
李澤厚:返回古典要建立在現代性基礎之上,不要現代性的古典是種倒退。西方社會發展到現在的確是有很多問題。但中國和西方相比,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仍然需要理性啟蒙。10年前我就講過,有的人是“蒙啟”,把啟蒙過的東西又蒙起來。我們首先要接受和采納普世價值,在這個基礎之上跟傳統結合,返回古典。這才可能開創新的東西,將來對全世界做出貢獻。這是我一直講的“西體中用”,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堅持這些東西。
工資太低夠不上“反動學術權威”
人物周刊:對于儒家的認識,您認為梁漱溟跟您是最接近的,您還跟他合過影。
李澤厚:對。梁漱溟當時還是反面形象。1982年,夏威夷的一次會議,邀請了梁漱溟、馮友蘭。馮友蘭去了,梁漱溟沒有去,不讓他去,其實他很想去的。跟他合影是犯忌的,1985年那次我帶頭跟他合影別人才跟著去。1989年后,有認識的人在院里看見我躲得遠遠的。政治氣氛的厲害,你們這一代很難理解得了。
人物周刊:別人躲著您,您是什么感受?
李澤厚:躲就躲,我不記怪你。
人物周刊:在政治運動壓力下,您有沒有批評自己的朋友?
李澤厚:很少。我的朋友很少。在運動中能逃避就逃避,能少發言就盡量少發言。我自己檢討寫了不少,寫過違心的東西,但很少批判別人。
人物周刊:沒寫過批判別人的文章嗎?
李澤厚:1964年批周谷城時,我寫過文章,還寫過一篇批電影《北國江南》的,是《人民日報》約的稿,都發表了。那時感覺一場災難要來了,我估計要搞第二次“反右”,知識界非常恐慌。當時我雖然年紀不大,但有點名氣了,所以得趕快出來自救,就寫了文章,以為這樣政治上就平穩了,其實太幼稚了。1966年5月《紅旗》雜志上有一篇文章是批評我的,嚇得要命,馬上寫了一篇文章辯駁,但沒有發表。
人物周刊:您是怎么躲過“反右”的?
李澤厚:主要原因是當時不在北京,到敦煌考察壁畫去了,所以有人說我是漏網“右派”。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哲學所內的“右派”比例太高了,超過了15%。
人物周刊:“文革”又是怎么躲過的?有沒有做讓自己內疚的事情?
李澤厚:基本沒有,“文革”中我是逍遙派,兩派都沒參加。我不是黨員,連團員都不是。我一輩子沒有對什么東西宣過誓。政治要跟人打交道,我就不愛跟人打交道。1966年我到北大看大字報,我名字打了叉。無論在哪所大學我都會最早被揪出來,但在學部(社科院),大人物多得很。有人說李澤厚有這么大的社會影響,應該算一個啊。一查工資太低,夠不上“反動學術權威”。
人物周刊:您很害怕被批判?
李澤厚:人都有本能,其中一種就是怕。那場風波之后抓人,我倒不怕抓,我怕被抓了以后挨打。當時我是人大常委會文教委員會委員,列席人大常委會。我在會場上被點了名。我想這下是不是要扣起來了?我幾乎是最后一個離開會場的。
人物周刊:為什么要最后一個走?
李澤厚:我以為要被抓起來了,坐在那里等著,結果沒有任何動靜,我就出來了。
人物周刊:好像歷次運動您都能幸運逃脫?
李澤厚:“反右”時說我是“漏網右派”,“文革”時我應該被批但沒被批。我政治上比較謹慎,注意掌握度,掌握度人才能生存。
人物周刊:在80年代您差點成為社科院副院長?
李澤厚:他們確實想提拔我當副院長,或明或暗說了多次,我因此遭到很強烈的反對。我對這件事興趣不大。這不是故作清高。當官有什么好處?第一是有汽車,對我不是很重要;第二是有秘書,我不需要;第三是房子大一點,但我后來住的房子和副院長一般大,對門就是常務副院長。而且當官有個壞處,要開各種各樣無聊的會。用3個沒必要的好處換這個壞處劃不來。我這個人一輩子最討厭開會,現在也是,包括學術會議,覺得無聊。
人物周刊:當時在所里什么職務?
李澤厚:胡喬木、鄧力群當院長時從助理研究員提了研究員,那是越級提拔了。我1955年進的哲學所,到1986年才分給我宿舍。我當了我愛人20多年的家屬(住在愛人單位宿舍)。宿舍是胡喬木當院長時分給我的,不是所里給我的,所里對我一直是壓制的。我最紅的時候,1979到1989年,《哲學研究》(哲學所刊物)每年12期,加起來120期吧,一共只發表過我兩篇文章,有案可查。他們不向我約稿,我知道我交稿子他們也不會用,但別的刊物會用。
寫了入黨申請書,又要了回來
人物周刊:前面您說您連團員都不是,但80年代您交過入黨申請書。
李澤厚:不是說要提拔我嘛,提拔的話首先要入黨。胡喬木、鄧力群都要我入黨,我不好說我不入。但我知道絕不會通過,因為哲學所對我有意見,我挨過整的,一些領導擔心我被提拔了他們的官位保不住。我寫了入黨申請書,又要了回來。他們再要我入黨我就不入了。
人物周刊:所以有人批評您圓滑。
李澤厚:我這人恰恰不圓滑。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就是因為我太不圓滑了。我的人際關系不好,沒什么人緣,每次回國周圍人都不知道,在美國也是這樣。我在香港一年,離開后沒跟任何人打電話聯系過,當然,別人打電話我是接的。有人認為我很傲慢,其實我是沒事就不聯系。學生不來看我也沒關系,因為我也很少去看別人,包括長輩。我給宗白華的書寫序,之前之后都沒有去看他。我從小受冰心影響,住皂君廟的時候,離她住所很近,也沒去看過她。
人物周刊:但任繼愈先生您去看過。
李澤厚:次數極少。現在感到愧疚的是,本來2008年是要去看他的,由于身體問題提前回美國了,沒有來得及去,現在變成遺憾了。
人物周刊:您在臺灣時,有人問您要不要去見牟宗三(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您也沒去。
李澤厚:我對拜訪名人沒興趣,不愛跟人打交道,不管什么人。
人物周刊:在臺灣只拜訪過證嚴法師?
李澤厚:那也不是我主動要去,是一個叫高信疆的朋友——現在過世了,帶我游臺灣一周,其中的一站是花蓮,證嚴法師在那里,他們關系很好,就帶我去了。證嚴法師在臺灣影響力非常大,是個真正了不起的人,值得去看。
人物周刊:和她有些什么交流?
李澤厚:她說人死在家里比死在醫院里好,醫院里是陌生人,家里是親人。佛家講的是脫離塵世,為什么想要死在家里呢?因為是初次見面,我并沒有問,但這給了我一個啟發,連那么一個高僧都有這種想法,儒家的東西無聲無息滲透到了佛教里面。
人物周刊:據說,這次回國您遇到了“文革”中非常有名的人?
李澤厚:碰到了戚本禹、閻長貴,我以前不認識。閻長貴當過江青秘書,戚本禹見過毛澤東多次。閻長貴送我的書的材料很重要,訂正了很多錯誤流言。這本書在國內公開發行,叫《問史》,寫江青。毛澤東什么時候決定結束“文革”,我根據材料判斷是武漢“7•20”事件之后,問戚本禹,他是當事人,證明是對的,很高興。我特別想了解毛澤東跟劉少奇、林彪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想半輩子糊里糊涂地被打發掉了。
人物周刊:為什么沒做些這類歷史研究?
李澤厚:很大一個原因是歷史不可信,很多材料都是靠不住的。有的人考證半天,根據材料得出一個結論,但那些材料本身不可信。發現歷史真相非常困難,你能得到60%就了不得了,很多10%都沒有。很多關于我自己的好的、壞的講法,都沒那回事。自己的事都是如此,更不要說歷史了。人活著,材料就這樣不可信,更不要說死后了。
政治民主不是非得馬上實現
人物周刊:您如何評價中國改革開放這30年?
李澤厚:這30年中國經濟發展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路。鄉鎮企業、宏觀調控、政府出面招商引資,這是外國沒搞過的,政府功不可沒。但要看到,因為政府干預,民營企業被壓制。中小企業發展好了,中國的經濟成就才能鞏固。
人物周刊:您曾提出中國現代化“四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您把政治民主放在了最后。
李澤厚:政治民主應該搞,但我覺得不是非得馬上搞。我始終首先強調經濟發展,而且要“社會正義”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搞“政治民主”。可以先實現黨內民主,建立輿論監督機制。不能一下鋪開,那就限定幾家報紙、刊物可以自由地討論,至少學術界可以討論,然后逐步放開輿論。我們可以慢慢走出一條通往民主的中國道路來。
人物周刊:伯恩斯坦“主張漸進改良,告別暴力革命”的思想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李澤厚:我認為伯恩斯坦是對的,但他沒有我講得清楚。恩格斯晚年表述過放棄革命、轉向改良的看法。我在1952年就讀到了。伯恩斯坦說這是恩格斯的政治遺囑。馬克思當年說過類似的話。修正主義是對的,我們反修是錯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所謂的“中國模式”?
李澤厚:中國模式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也是我在20年前提出,而且在90年代的文章里反復說的:不要一味模仿西方,要走自己的路。但現在“中國模式”遠遠沒有形成。包括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還沒實現,很多地方其實是“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比如大學官本位太厲害,這是不對的。就連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科學家出來官員都是往后退的。王國維、陳寅恪他們都沒什么“長”字頭銜,現在很多學者向“長”看齊。
人物周刊:有人說您給中國指出了一條道路,但顧準和王元化指出了更好的道路。
李澤厚:我不知道他們指的是什么道路。王元化的書我是看的,他對我也不錯,但他到底講了什么我并不清楚。顧準是很不錯的,他和陳寅恪的人格很了不起。不過陳的專業是中古史,真正看的人少;顧研究的是西方自由主義,并無獨創。他們影響別人的主要還是人格,這是中國的道德主義傳統。陳寅恪在他那代學人中是惟一一個沒投降的,而且比較清醒。顧準下放時和我們在一起,人很理性很直爽。他是不幸的,連家人都不認同他,跟他劃清了界限。
人物周刊:有人提出一個說法:中國從1949年到2009年,前30年的關鍵詞是“政治”,后30年是“經濟”,今后30年可能是“信仰”。您認為今后30年,中國人最需要解決的是不是信仰問題或價值觀問題?
李澤厚:信仰問題是不可能統一解決的。不用等30年,現在就要意識到,這個問題會越來越突出。這是人為什么活的問題。人首先要活著,才有為什么活著的問題。活著都成問題的時候,大家就會拼命賺錢。物質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大家就會追問活著是為什么。明白怎么活不是那么容易的。
人物周刊:現在的人都強調“個性”,所謂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特別是年輕人極度張揚自我,會不會產生一些問題?
李澤厚:我始終認為嚴復翻譯穆勒《論自由》時用的“群己權界”這個詞是很好的。個人領域不能干涉,妨礙到群體就不行,重要的是權利范圍的界定。
人物周刊:所以您主張把宗教性私德和社會性公德分開來?
李澤厚:要把這兩種道德分開。宗教性道德說的是個人的安身立命。你要做圣人可以,不能強迫每個人做圣人。但一個社會有必需的公共道德。過馬路看紅綠燈,這是社會性道德,首先要尊重公共秩序。
腦科學能解決神秘經驗問題
人物周刊:美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您最看重哪個家?
李澤厚:思想者,英文里是thinker。我同意海德格爾的觀點。海德格爾說哲學已經專業化,他愿意做思想者。美學家是不成立的,我最討厭別人叫我美學家。國內喜歡拿海德格爾和老子比,我不贊成。我把海德格爾的哲學叫做士兵哲學,他是向著死亡制造了一個深淵。二戰之后打掃戰場,發現一些德國士兵帶著海德格爾的著作。說了半天我要說句狂妄的話:我就是要以儒家的東西解決海德格爾問題,至少我的目的是這樣的。儒家講情,主張從具體的日常生活中獲得生命感。
人物周刊:作為一個人文學者,您會關心自然科學領域的進展嗎?
李澤厚:我不很了解,但非常關心。最近這幾年,我特別關心腦科學。我認為21到22世紀,科學的進展將集中于神經生理學,心理學必須建立在生理學基礎上。我最近的封筆文章是講宗教的。宗教最根本的是神秘經驗,修煉到了一定程度,感覺自己到上帝那里去了。
人物周刊:您有過這種經驗嗎?
李澤厚:我沒有,但我相信有,因為有很多記載。我認為將來腦科學可以解決神秘經驗問題,因此也就不再神秘了。這對所有宗教都會是一個大打擊。上帝就在你腦子里。我現在相信腦科學中的達爾文主義。
人物周刊:80歲了,覺得自己的生命夠豐富嗎?
李澤厚:不豐富,主要是因為毛澤東時代。但在這一代人中,我爭取了最多的自由時間。我有兩大“滿意”,這是一個。另一個是,60歲到國外去,又打了一個天下,62歲學車,還用英文上課。我的英文不好,這很不容易,我居然克服了。我在經濟上能獨立自主,不依賴任何人,這也很滿意。
人物周刊:你們這代人最普遍的問題是什么?
李澤厚:我們是馴服的一代,誠實有余,聰明不足。我們這代有很多人為了向黨交心被打成“右派”。
人物周刊:有沒有特別脆弱的時候?
李澤厚:我不認為自己是強悍的人,但也還不那么脆弱,不然早死了。我想得開,很多事無所謂。但我自我感覺不好,挫折感比較強,小事我都會有失敗感,從沒對自己滿意過。
人物周刊:哪些時刻是脆弱的?
李澤厚:現在怕出去,難道不脆弱(當時是冬天,天冷,待在屋里)?再強大的個體也是渺小的。人貴有自知之明,認識到自己只有那么一點點力量就會專注于自己能做到的事。
人物周刊:您的學說倡導樂感,為什么自己的心境那么苦?
李澤厚:不是苦,是自我感覺不好。A型血的人比較容易跟自己較勁,我是比較典型的A型血。我太太也是A型,但個性很不一樣。所以我想研究血型,應該還可以分出許多亞型。
人物周刊:您有感覺孤獨的時候嗎?
李澤厚:我這輩子都在孤獨中度過,不孤獨的時候是少數。遇到困難的事,比如說遭到批判了,我是不跟太太說的。這是一個男人的基本原則。
人物周刊:孤獨是不是也成就了您?
李澤厚:要看是什么樣的孤獨,孤獨也有很多不同的類型,有的是客觀上的孤獨,有的是內心的孤獨。在毛時代我經常被批評的3點是:不暴露思想、不靠攏組織、不接近群眾。當時都是大問題。我是地下思考、邊緣寫作。我靜悄悄地寫,也有一批靜悄悄的讀者。我的書一直賣得不錯,包括一些難懂的書,寫康德的那本書也有盜版的。朋友跟我說我還不相信,他就找了盜版書給我看。
在美國沒有人知道我
人物周刊:90年代初,為什么去了美國?
李澤厚:那場風波后,國外有很多邀請,中國政府說只要沒刑事問題就可以出去。所以我并不是跑出去的,是拿著外交部護照大搖大擺出去的。
人物周刊:去美國是當時最好的選擇嗎?
李澤厚:我認為是最好的選擇,現在也不后悔。
人物周刊:那樣的年紀去美國對您是很大的挑戰吧?
李澤厚:很大的挑戰。我可以留在國內,也不會把我怎么樣,也許像王蒙那樣,還會被捧為大師。我不羨慕。商人好利,學人好名。我也承認我20多歲時特別好名,不是說現在完全不好,但是已經不怎么好了。我愿意干的事情我自己滿意就行,管別人認不認識我呢。演員主要靠表演,做學問主要靠經得起時間考驗。
人物周刊:在美國的大學里主要講什么?
李澤厚:講思想史和美學。美國沒人知道我。
人物周刊:從獨領風騷到默默無聞,沒有失落感嗎?
李澤厚:我不在乎,我始終就是個普通百姓。
人物周刊:但因為您的關系,您的家人也要去美國。怎么看個人對家庭的責任?
李澤厚:我一直主張有家庭,家庭的感情不是其他感情能代替的。但不是說人這一生只能愛一個人,只能跟一個人有性關系。我覺得可以開放些,男女都一樣,可以有妻子和丈夫,也可以有情人。發現對方有情人就分手,我認為是很愚蠢的。從性心理學上來講,都希望獨占對方而自己有情人,女的也這樣,男性更強一些。
人物周刊:您本人也是這樣做的?
李澤厚:我是這樣做的。我還說過老婆必須漂亮,情人不一定。老婆是天天要面對的現實,高興也好,不高興也好,她漂亮一點你的氣可能就少一點。情人沒關系,生氣就分開了,在某一點上談得來就不錯了,補老婆的不足。我認為這是有道理的,
但我不要求每個人都像我這樣認為。這是個人自由、個人選擇。每個人的生理和心理情況不一樣,自己決定,不要用一般的觀念來捆住。這點大多數人想不通,想不通就想不通好了,也是種選擇。
人物周刊:這些您太太都知道嗎?
李澤厚:都知道。
人物周刊:她知道了也沒有問題?
李澤厚:有問題我們不就離婚了嘛。我愛人喜歡哪個男人也可以啊,結婚時我就跟她講過。
人物周刊:兒子怎么看您的成就?
李澤厚:他大概并不清楚我有什么成就,他沒看過我的書,我也并不要求他看,包括我的學生我都不要求,太太也如此,我的很多書他們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版稅她也不管嗎?
李澤厚:我太太只管花錢,她不管來源。哈哈,我值得驕傲的一點是我太太一生沒有為錢煩惱過。
人物周刊:您沒有想過讓孩子繼承您的事業?
李澤厚:從來沒有,在他出生之前就決定不讓他搞文科了:第一,文科比理科難。文科寫兩篇文章是很容易,但真正要做出成績來是很難的。理工科只要你夠認真,不管怎樣都能做出點成績;第二,當時是毛澤東時代,搞文科很危險,搞不好就打成反革命了,從安全考慮也不讓他搞文科。我很注意培養他的數學,我認為數學是理工科基礎。
人物周刊:有沒有想過抱孫子這個問題?
李澤厚:沒有。這比較特殊些,是個性問題。我不相信什么傳宗接代,我這輩子見不到孫子都沒關系,我不重視這些。
我準備將來把腦袋冷凍起來
人物周刊:您打算怎么過80歲生日?
李澤厚:一家3口在家吃頓飯就行了。很多人要給我做生日,我拒絕了。我說40、50、60都可以做,過了70就不要做了。有人說祝我活到90歲,我不愛聽,沒意義。劉再復原來想給我出本書紀念。我說,一是我不參與,二是你做不成。
人物周刊:沒考慮過寫自傳?
李澤厚:很多人勸我寫,余英時、何兆武都勸過,我不愿意。
人物周刊:這個時候還不想說?
李澤厚:這個時候不說就一輩子不說了。我過一年算一年,現在還能跟你們談話,也許明天就不行了。
人物周刊:還有沒有特別想完成的事情?
李澤厚:老了,想做也沒法做,我耽誤了20年。我不希望痛苦地死掉,死還是要死的,我怕痛不怕死。我希望我死的時候,除家人以外,誰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您欣賞誰的生活境界?
李澤厚:喜歡陶淵明的。
人物周刊:從個人來說,您感覺什么時候比較幸福?
李澤厚:當然有,但不能講。人在身體和精神都感覺愉快時最幸福。
人物周刊:性愛?
李澤厚:性愛也有很多差異,做愛不僅僅是那一個時刻,還涉及兩個人的關系。各人靈肉的比例——心靈比例有多大,生理比例有多大,恐怕有很大差異。有的純粹是身體的滿足,柏拉圖那種純粹精神上的滿足我不大相信,但也可能有。
人物周刊:您現在的生活幸福嗎?
李澤厚:我說過我自我感覺不好。但我也不覺得不幸福,現在能活著就不錯了。那么多政治磨難都逃過來了,應該說很僥幸了。
人物周刊:據說您12歲就有過精神危機?
李澤厚:當時想,人總是要死的,活著為什么?
人物周刊:現在您想清楚為什么活著了嗎?如果寫墓志銘,您會怎么總結此生?
李澤厚:有的人為名為利活,有的人為兒女活,有的人為國家民族活。我的意愿跟馬克思差不多,為人類活,所以我有本書叫《人類學歷史本體論》。我現在是靜悄悄地活著,也準備靜悄悄地死掉。
我不會有墓志銘。但我準備將來把腦袋留下來,冷凍,過300年,或者500年,再拿出來。這件事情我都向老婆孩子交待好了。在美國有很多人已經這么做了,有的人是想復活,我覺得復活是不可能的。我是想證明文化是不是影響了大腦,幾百年后,是不是可以從我的大腦里發現中國文化的殘跡,證明我的積淀理論。如果證明有影響(文化影響大腦),我覺得比我所有書加起來貢獻都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