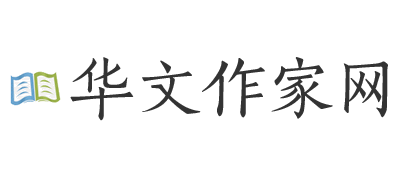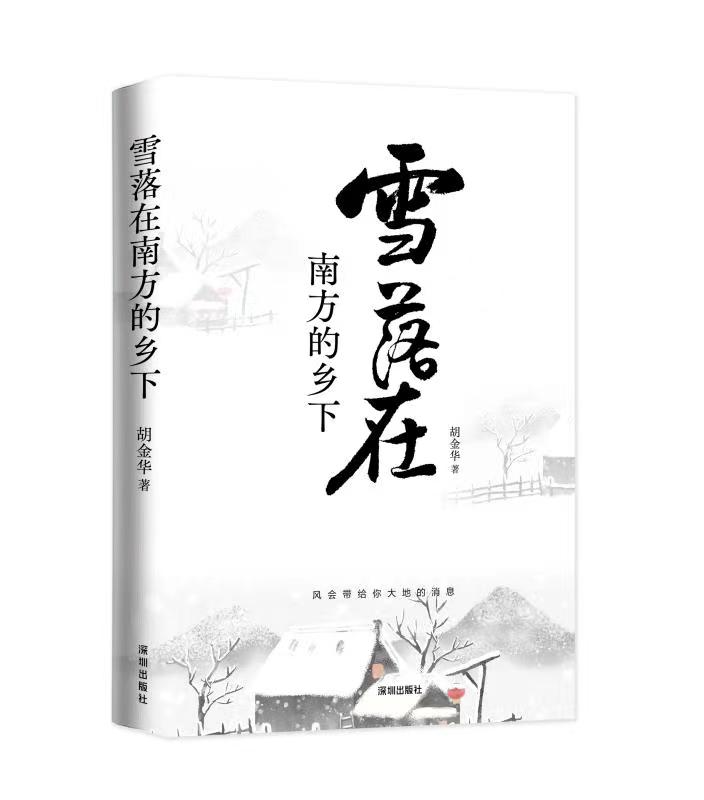
胡金華是詩人中典型的大器晚成者,少年時便懷有做詩家的夢想,因誤入仕途多年不鳴,但始終念茲在茲,近年來一鳴驚人,大作常見《詩刊》《湖南文學》等大刊外,不經意間又捧出了一部厚重詩集《雪落在南方的鄉下》。燈下黃昏,細細品讀這部作品,只覺眼前雪花飄飄灑灑,不只落在南方鄉下,還飄在讀者心靈,韻味像清光般漫涌。
著名詩人余光中說:“好的詩歌應該包括作者想象力的豐富,語言的高超,講究音調和意象的營造。一句話:深入淺出,通俗易懂。”這大概是從唐詩宋詞、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詩歌,以及一些西方詩歌經典概括出來的經驗,經得起時間的淘漉與檢驗。胡金華筆下發自至情至性,或憂傷或灑脫的詩句,頗合余光中的標準,因而無疑是難得的好詩。
這部詩集令人沉迷之處,首先是想象的奇特與豐沛。譬如“生活是塊臘肉\只是高掛在終日熏烤的火堂(《金子村》)”,“一條石路通往村前的缺口\老婆婆打落的牙縫(《一個古村的新生)》”,一把篾刀\削薄自己后半生的命(《篾匠》),這些妙手偶得的詩句,詩人的聯想與想象自然、親切而奇特,令人不禁會心一笑,激賞不已。詩人在曾國藩故居富厚堂前凝神《聽雨》,更是浮想聯翩,已至上下數百年,縱橫幾千里:“正好倚門聽雨\聽著聽著\有瑯瑯書聲\有金戈鐵馬的吶喊聲\有船過衡陽、岳陽、安慶、天京的槳聲\我聽到了一部湘軍歷史的濤聲。”這磅礴的濤聲,像琴弦上奏出的旋律,將讀者帶入了一幅幅金戈鐵馬的壯闊畫面。
詩歌是語言的藝術,古人為“吟安一個字”,表現出最美的意境,常“拈斷數莖須”。胡金華也有自己遵循的詩歌創作原則,其中之一便是“要有詩意,努力寫得有韻味和畫面感”。因而他的詩句語言除了余光中所說的“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外,也頗具凝練之美,在瑰麗與雅致間捧出夢幻般的圖景。有時候,詩人的語言看似與常識相背離的無理,卻存貯了意外的美感與痛感。
其《母親印象(組詩)》中,“一張床、一床被\我選擇三伏天出生也許為了節約\娘和我打地鋪\根根稻草能扯出我青澀的童年”“兒女的補巴象細作的田地\半夜的月光也不放過”,三言兩語便勾勒出了寒門子弟出生與成長的辛酸往昔,以及父母撫養兒女的不易。《石匠》一詩中,“外公一輩子酷愛石頭\九十歲時還給自己鑿了石墓\留下一處空白要我媽媽和舅舅填上”“每年新年和清明\我們祖孫倆隔著石頭打望\習慣沉默的外公總是不作任何聲響”,詩人以素樸凝練語言構筑的意象里,不僅有石匠外公技藝高超,永不服老的美感,更有令讀者灑下清淚的痛感。
而《泥瓦匠》中“青煙沒了\我的童年沒了\泥窯和往事都長滿了茅草”的句子,則以看似平淡的漢字與詞語藝術組合,構筑出飽含神韻的意境,令無數有過鄉下童年生活的讀者悲從中來,詩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妙筆,也得到了深邃體現。
胡金華的詩集里還有著熾熱而綿長的親情與鄉情。沈從文的墓碑銘文說:“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說的是士兵,其實是沈從文這樣深深眷戀故土的文人。同為文人的胡金華自然也如此,他出身南方鄉下,常年在千里外的他鄉工作,故鄉始終夢縈魂牽于心,見于筆端,便是汩汩滔滔的詩情。他曾說:“我自己最喜歡寫鄉村的詩,試圖寫好鄉情親情,描繪那種真實的、淡淡的的鄉愁。”
《鄧家灣》一詩中,詩人說自己老家“如一粒稻谷散落在湘中一角\怎么描繪也畫不全也不重要”,但實際上在其心中有千鈞之重,“一顆小石丟入附近的漣河還有水花\誰人會關注水里還有一只小蝦\可我不能不關心和愛啊\那是一個游子魂牽夢縈的家鄉”。他筆下的《赤腳醫生》“熱天,真的是一雙赤腳\腳板,象鐵,仗量著生養的地方\鋤頭,始終扛在肩上\藥廂,總隨身攜帶\象農墾戰土屯守邊疆”,實際上是童年的鄉村記憶與溫馨懷念。這種揮之不去的鄉愁,詩人用功頗多,巜雪落江南》《母親印象》《散落天堂的愛》《清明進山》《與生俱來的病》等都是可圈可點的代表作,其中“從炊煙里走出要斷炊煙”“鄉下從來不喜歡設卡抬杠的人”等,可謂既富詩韻又頗有哲理的佳句,詩人也不無自得地說:“這是我最喜歡的詩句。”
這部詩集的精妙,自然不只有我讀出的這幾點,胡金華行走異鄉數十年,身體與靈魂遭遇的困厄也自然非止一端。然而,一切苦難與磨礪最終都是詩,他在退出俗務回歸山水之際,將所有一切化作筆端源源噴涌的才情。我想,作為“艱難險阻備嘗之矣”的政壇卸任者,他筆下的雪花將更為絢美多姿,在詩壇的后續之功也將更為輝煌。作為同鄉,我充滿樂見其成的殷切期待。
作者簡介:
張雄文,中國作協會員、湖南省作協全委、株洲市文聯副主席、市作協主席。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人民文學》《中國作家》等報刊發表百余萬字,出版《名將粟裕珍聞錄》《潮卷南海》《燕啄紅土地》《白帝,赤帝》等書四百余萬字。曾獲冰心散文獎、山西省五個一工程獎、四川散文獎等多種獎項。